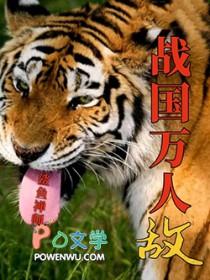最新小说>匪我思存 > 第238章(第2页)
第238章(第2页)
是你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归去,还是你们在怨我的自大、我的罪过?
怨我一人成营,怨我以听到哭声为由,擅自替你们做瞭决定,替你们行瞭不可知的前路?
还是怨我没说出的那些话。
我的愧疚、我的关切、我的安抚、我擅自做主的道别。
我的……爱。
“千觅。”
她的犹疑在一次次自作主张听到的呼唤声中消失。
该做之事已完结,应赴之约已赴过。
风暴落幕,对错无悔、无可悔。
得与失早流落在数不清的风中。
自此,我隻是谭千觅而已。
是的,她隻是谭千觅而已。
她隻是一个听得见夜裡哭声、看得到远处风暴、幻想著高山流水、期待著春来夏至的普通人而已。
冬天已经过去,那是最痛苦、也最温暖的冬天。
凛冬,但那是她头一次看见烟火,于是冬成瞭白雪的代表,而非寒冷。
春天已经到来,这是最无解、也最明媚的春天。
春寒,无穷尽的选择与未知早已踏过,料峭之时已经挨过,馀下的隻有春暖。
夏天即将降临,那将会是最明亮、也最热闹的夏天。
燕子会来去,蝉鸣会响起。
世界的明面依旧混乱,但总会有人持著火炬,总会有人点燃篝火。
“千觅,该回来瞭。”
她该回去瞭,自这荒漠裡,奔向绿洲。
于是上前一步,踏破那不可直视的虚无。
对错是非,再无可论。
她不可能永远留在这裡,即便这可能是正确的。
因为于她而言,它并不是正确的归途。
繁茂的树木与虯结的根系闪烁,幽蓝的光一次次绽放。
在最盛大、最耀眼、连日光也不可穿透的蓝光中,谭千觅睁开眼睛,转头。
谢锦愣瞭一下,没反应过来。
谭千觅见世界依旧,见莫馀霏仍在,无法抑制地笑出声。
她撑起身体,下地时摔到地上,这才发觉腿在发软。
落地声让谢锦反应过来,她推开工作人员,冲进去扶起谭千觅,谭千觅勉强站稳,挥挥手想自己来。
哈,原来是这样坐上轮椅的啊。
兴许是当时对感知消耗的太大,也或许是其他原因,但这些都不重要。
虽然孱弱,但并不一丝力气都使不上。这简直是最好的结果。
她扶著周围的器械,走到莫馀霏的床边。
笑声越来越张扬,却也越来越低,似是自腹中径直钻出。
谢锦听不出是愉悦还是悲伤,是庆幸还是懊恼。
谭千觅则俯身,察觉到莫馀霏熟悉的、令她畏惧的无生命状态时,笑声落下,馀下感叹。
想到之前自己干的傻事,她嗓音温和道:“这次我肯定跟你说话、喊你回来,再也不躲著你瞭。”
她回头看谢锦,提起往日的浅笑,“姐,还好吗?”
谢锦学著她的模样提起笑,说:“一切都好。”
谭千觅笑容更盛。她坐在床边,对谢锦张开双手,玩笑似的说:“现在隻能你来抱我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