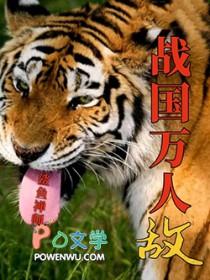最新小说>璇天变 作者live > 第43章(第1页)
第43章(第1页)
原来这不周山本是上古天柱,立地而擎天,托起宇宙洪荒。然后有祝融之子共工,与帝颛争夺帝位,不惜兵戎。可惜共工虽勇,终不敌帝颛之兵,败退不周山下,乃见擎天巨柱阻挡其道,一时愤慨,头触不周,竟将那撑天柱地的不周山拦腰撞断。
天柱断,穹苍倾,日月星辰西落,夕入凡间。
东方塌,南地陷,故有水往东流,百川归海。
而这不周山,虽断而再难擎天,但山仍连天,成世人梦寐之梯。
他们在山脚停步。
离契让天璇落地站了,便化出人形,抬头看这不周山,便是近了,更觉此山巍峨。山体上并无密林,光秃秃的怪石嶙峋,且无上山栈道,峰顶积雪封山,即便时已夏深,亦无冰融。
石岩之间立有枯萎巨松,灰败枝条仍如臂膀延伸向外,离契正要迈步,却被天璇拉住。正是不解,却注意到天璇眼中示意,顺他视线看去,只见原来在那巨松枝上,静静栖息了一只只腹大如壶的巨蜂!
天璇皱眉道:“是玄蜂。”
他口中所言玄蜂,乃上古天兽,腹有剧毒,蛰人必死。玄蜂体形虽小,但有凝聚之能,往是一蜂动,而群体出,其数之众足以遮天蔽日,若被玄蜂群缠上,莫说你是一介凡人,便是洞中上仙,亦摆脱不得。
离契听过其中厉害,不禁握了天璇手掌,稍稍一紧,压低声音免得惊动蜂群,道:“蜂毒于我无用,待我把蜂群引开,你先闯过去。”
说罢,离契便要去引玄蜂,岂料手却被天璇牢牢拽住。
虽说狼妖有避邪辟毒之能,但看那玄蜂股上蜂针,粗长如玉女簪般,即使不会中毒,被它戳上也是异常疼痛,更况要面对的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玄蜂。离契想必也是知道,故有意引开蜂群,免他受伤。
天璇有些着恼,离契不愿见他有伤,难道自己就可以看着他被蜂群蛰成破烂而却视若无睹施然而过?
“你给我站好了。我去。”
他还未及迈步,已被牢牢抱在结实的怀抱中。
离契的臂膀紧实得如同铁箍,勒得他动弹不得,天璇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想要勒断自己的肋骨。
狼妖将头压在他的肩膀上,声音有着不可思议的压抑。
“为什么……你总是不愿让我帮你……对你……总是……我总是觉得无能为力……”
是的。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能做饭,可天璇不吃的。
他烧起炉火,可天璇不会冷。
他准备温暖的被褥,可天璇不需要睡觉。
天璇有足够的能力,即使没有他,星君也能独自破妖域,闯不周。
然后有一天,他完成了天界的使命,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离开,再过千年,他便会彻底忘记曾经有一头黑狼妖,在短短的如同眨眼般的短暂里,伴他左右。
想到这里,他的心脏就想被一只手紧紧拽住,越捏越紧。
可天璇,却仍是如初相识时那般,淡漠的样子。
他可以在岩石上看书,一看便是一天。
他可以游走林荫山溪,一走便不知日落。
他可以观星像揣天机,整夜地站在屋外。
或许再过千万年,天璇也不会改变。
即使他夜里总是悄悄地搂紧天璇,却总不禁会想着,天亮时,怀里会否只徒剩一具冰冷的躯壳。
从未感受过的彷徨在心的深处蔓延着,离契只是徒劳地掩饰着,但空虚,却像烂掉的苹果上的腐俎,不断蚕食着余下的一切。
似乎是感觉到了他的异常,天璇没有挣扎,只任由他紧紧地困住自己。
这只坚强的狼妖总会在他看不到的角落露出神伤,却在他回头的瞬间用笑容掩饰,甚至不惜动用幻化术,小心翼翼地将心里的情绪掩藏,不愿打扰他的静修。
或许离契自以为掩饰得很好,但事实上,再高深的幻化术,也无法掩藏狼妖双眼中不堪一击的脆弱。
天璇轻轻地叹息,伸手抚上离契有些凌乱的长发,想起相遇初时他那硬气倔犟,即使面对强敌仍是不折不挠的顽固,如今却每日如履薄冰般担忧着什么,每当看到这样的离契,便总是想与他说,“我不会回去。”
然,可以么?
他自嘲,星君真身在天,这副躯体纵有他元神维持,总有一日,难免腐败,介时,便是他再不愿意,还是得重返天庭。
没有天帝谕旨,他又如何能再度下凡。他没有天枢那般降魔伏妖的能耐,自不会时常受天帝调遣。难道要像开阳那般,悄悄避开了天兵神眼,溜下凡间?即便如此,亦难长久……
他,又能为他做些什么?
难解的困局,便像麻乱的蔓藤纠结在心。
许久,天璇感到离契放开了些许,然后退开半步,依旧露出那恍若无事的笑容。
“抱歉,我一时失态了。”
天璇却是皱眉,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笑容扭曲得如此勉强?
猛地伸手扯住他的头发,在狼妖吃疼呼出声来时,吻住了有些粗糙的嘴唇,细细碾咬。离契始时吃惊,但很快便被凉凉的嘴唇与舌头俘获了意志,本能地探出舌头,卷住对方,交缠。
在他正要伸手去搂天璇的腰背,欲加深这刻的接触,天璇却退开了。
漆黑的眸中有着一掠而过的欲念:“你并不需要道歉。”声音低哑得连自己都觉得吃惊,这副身体居然本能地产生了情欲。体内的妖气也在不知不觉间骚动起来,天璇强自压下紊乱的气息,转开了视线,不去看离契失落的脸庞。
他拿起乾坤袋:“给你气糊涂了,我这正好带了玄蜂最喜之物。”他边说着,边从里面找出一株绛紫色皱皱巴巴的花骨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