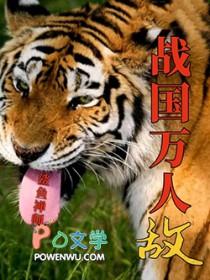最新小说>西关小镇 > 第5章 交锋烫手山芋(第2页)
第5章 交锋烫手山芋(第2页)
郁贲面色冷漠。
关晞说:“听你的口音,你是北方人?”
郁贲瞥了关晞一眼。
他确实是北方人,如果不是因为施远,他才不会在南方工作。
刚好席上有人听见,笑着问:“关小姐,您是哪里人?我猜猜——江浙一带?”
关晞笑着摇头:“北方人。”
那人饶有兴致:“北方哪里人?”
关晞说:“沈阳人。”
旁边人指着刚刚说话的人:“这位以前在沈阳外派过三年,你们必须喝一杯。”
关晞立刻起身敬酒。对面人和他酒杯一碰:“关小姐,完全听不出口音。”
关晞一饮而尽:“我读本科就过来了。口音改得早。您在哪里外派的?”
那人说:“老工业区,铁西。”
关晞笑道:“巧了,我正是铁西人,工人村长大的工人子弟。”
那人笑笑:“关小姐,咱们有缘,必须再喝一杯。”
关晞又倒了杯酒,两人碰杯,她又一饮而尽。
坐下以后,关晞用茶水给自己洗餐具。
郁贲注视着她的动作。
他和她,算是半个老乡。
她和他的老家,都没有用茶水洗餐具的习惯。如今他们把自己根植在另一片土地,努力生存下去。他不知道这样洗餐具有什么意义,但腹诽归腹诽,依旧会入乡随俗。
民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有人又问:“关小姐怎么会跑这么远的?”
关晞笑着说:“我学文科,老家不好找工作,待遇也不行。”
“确实,老工业基地缺政策扶持,经济发展掉了队,可惜。”
“说起来,90年代下岗潮,和现在的裁员潮一模一样。老工业基地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
郁贲压低声音:“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关晞拿起筷子:“我是来帮你的。”
郁贲反问:“你在会议上放炮,把工程部的方案炸得灰飞烟灭——这是帮我?”
关晞不解释:“按照‘大拆大建’的思路,长乐坊项目不会有进度。”
郁贲的克制即将告罄。他等着关晞说下去。
关晞说:“我这次走访原住民,你知道,这些老房子,产权构成有多复杂吗?”
郁贲接过关晞递来的手机,越看,眉头皱得越深。
关晞说:“比如,312号二楼,区区30平的房间,产权人足足有11位。320号三楼的阿婆有八个兄弟姊妹,其中4个早年移民国外,如果你要拆迁,就必须得飞去国外拿到授权。长乐坊有多少户人家?你去谈拆迁补偿,你怎么谈得过来?而且,长乐坊全是老人家,拆迁中期,你打算怎么安置?如果老人家出了点问题,算谁的?”
郁贲面色沉沉,看不出想法。
半晌,他把手机还给关晞:“这些数据,刚才你在会议上没放出来。”
关晞似笑非笑:“这能在会议上放吗?你不觉得敏感?”
郁贲一怔,脑中仿佛突然被什么点亮。
他想起,施远在会议上问出的“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怎么回答的?
用来拆迁安置的资金。
很显然,施远想听到的不是这个答案。
郁贲皱眉思索片刻,渐渐回过味来:“长乐坊要拆,放了10年也没拆掉,问题不在于资金和施工团队,而在于——各种意义上的‘老’,产权结构过于复杂,导致多方扯皮推诿所隐含的成本。”
关晞点头:"有些问题不能克服也要克服,有些问题能克服也不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施远不希望你克服,你不但不能克服,还要据理力争,大吵特吵。"
郁贲冷笑一声:“长乐坊竟然是李卓秀甩给施远的烫手山芋,对吗?所以施远不好明说,指望我来做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