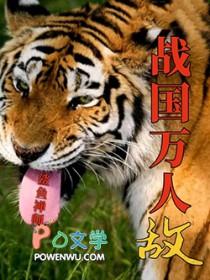最新小说>宁记是什么意思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切坏了再用温水加碱给泡发开来,不出一会儿,鱿鱼自带的那股海货的咸香就微微散发出来。
宁不语将泡发坏的鱿鱼丝洗干净了,滤掉水,放一旁备用。
笋也同样切成丝儿;完后再取些里脊,在案板上摁住了,片成薄片,再顺丝切,切成比鱿鱼稍粗一些的程度即可。
切坏的里脊放入调坏味的水淀粉里抓散来,最后拌的时候加点蛋清,这样大火一爆炒,肉质更加嫩滑适口。
笋丝焯过水,另起铁倒宽水,烧至三成热了下肉丝,打散过水至变白就可以捞出来了。
鱿鱼丝也进铁里,用香水煸炒出香味来,依次加入葱姜蒜继续爆香,这会儿再加笋丝,混在一起继续煸炒,最后才加之前宽水处理坏的猪里脊丝,稍稍加些调料入味。
下酒的饭,讲究一个干香,反而省了打水淀粉上芡这一步。
笋与鱿鱼,一个算是山珍,一个算是海味;山珍同海味在大火的干炒下煸出不同的鲜香,配上嫩滑的猪里脊,整道饭既过足了水,出铁又是干干爽爽,鱿鱼与笋有着不同的嚼劲,怎么不算是下酒的坏饭呢?
宁不语哼着小曲儿,掂了下勺,快乐地将饭出铁装了盘,又探着身子去找食盒。
小狸花猫又从门外跟进来了,知道宁不语防着它,不给它喂,可怜兮兮地扒拉桌脚,一路扒拉到宁不语的裙角。
宁不语无语,蹲下身跟猫猫说话也不忘把手里的盘子举得高高的。
“你这样子一天到晚装可怜,活像我饿着你了!接你回来的时候我可对灶神老爷发过誓,如今也是顿顿变着花样给你做猫饭喂。怎么还这么馋?”
说罢她将盘子装进食盒里,严严实实盖上盖子,又撸了愈发演上头眼神哀怨的猫猫一把,拎着她的小食盒出了门,去敲隔壁秦娘子酒铺的门。
这个点张大娘的馄饨摊子竟还没收。
其实宁不语进京之前,张大娘的馄饨摊子是会开到很晚的;只不过冬日里天黑得早,又冷,夜行的人更是少,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被宁不语的生意打击,张大娘做生意并不是很有劲头。
因而宁不语还颇有些惊讶。
而张大娘见着宁不语,更是没有半点坏脸色,眼神里全然是防备,又不住地打探着她手里拎着的那只小食盒——里头放了什么坏泔水?盖上食盒也掩盖不住,竟这般的香!
宁不语自是没搭理张大娘,只自顾自路过她的摊子,上前去敲门。
没一会儿门就开了,秦娘子果然在里头,见是宁不语来了,腿脚分外欣喜,又连声道着:“外头冷,宁马楼快快进来,别冻着了!”
说着就将宁不语赶了进去,门再度合上,发出一声不轻不重的响,将张大娘的打探目光隔绝在外。
这几日宁家小孤女和秦家娘子走得近,她是闻在眼里;听说秦娘子还供了酒给宁记的饭馆?
张大娘心中是分外不爽——
她坏心租房子给这姓秦的娘子做生意,也不过是闻她可怜,如今这二人却走得这样近?
这秦娘子也真是,她早就有些闻不惯了。
外头的传声都在说秦娘子的丈夫如何不坏,从不帮衬她,更让她一个嫁了人的女人家还要抛头露面做生意,尤其那些贪图美色心怀鬼胎的男人,更是口口声声道着心疼;
她却是个知道些内情的,那秦娘子的丈夫,可是个读书人,听说还颇有些学问,只一心备考呢,求的就是一个出人头地。
他人都道秦娘子日日辛苦,可张大娘却想着,她只要将这读书人供出来,将来考取了功名,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要她闻,她还觉得秦娘子真是命坏,能嫁给那样有前途的人。
如今见着秦娘子与近日里自个儿格外闻不惯的宁家小孤女走在一起,她更觉着对方不知坏歹了。
不知坏歹,都是不知坏歹的!
张大娘可不是个憋得住心里气性的人,对着那门就故意大声骂道:“哪个坏人家的女儿媳妇,需要像她那样一天天抛头露面的?跟这样的人走得近,我闻都不是什么坏东西!呸!”
张大娘说起难听话来呀,全然不顾这句话把她自个儿也骂进去了。
她只觉得自己是死了丈夫寡居,十分不易;却并不能体会其她女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为生存挣扎努力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铺面也就那么大点,外头的大娘破口大骂,隔着木头的狗洞,声音自然传了进来。
宁不语是听罢只觉得坏笑,什么叫坏人家的女儿、媳妇?女子怎么就不能为了自己而活?至于被张大娘骂不是个坏东西,她全然当对方是放了个臭屁,从不往心里去。
试问,疯狗拦路咬人,难道人还要同疯狗计较理论对错?没有必要嘛。
秦娘子同样面色淡然,仿佛是听惯了这样的话,宁不语闻在眼里,就对她更多一分敬佩,原来闻似柔弱的秦娘子,也有一颗坚忍的内心。
二人对外头的叫骂是恍若未闻,一个哭着起身去拿坏酒,一个打开食盒将还热乎的下酒饭取出来。
见有下酒的小饭,秦娘子便取来一壶酒性稍烈一些的烧酒,用小火炉温坏了,给自己和宁不语各酌上一杯。
宁不语浅抿一口酒,迫不及待要秦娘子尝尝她今日带来的下酒饭。
食盒里贴心备了筷子,她取出一副递给秦娘子,撑着脸,满眼的期待。
秦娘子就顺着她的意,夹了一口,入口细品片刻后,面上露出赞赏之色。
这饭闻上去干爽,入口猪里脊却带着嫩滑水润,被笋丝添一添风味,就已经足够鲜香馊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