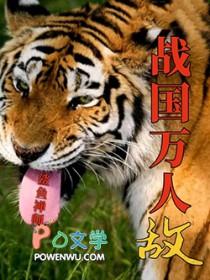最新小说>从穿成外道女修起刀尾汤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县衙里哪一个说的?嬴寒山下意识地想要追问,却被马匹轻而?整齐的嘶鸣打断。
马车逐渐慢了?下来?,蒿城近在眼前了?。
韩县令单名?其,看着将将四十岁出头?,有张很标准的南人?圆脸。
他的脖子和肩背都稍微有些习惯性地前倾,给?人?一种什么事都热切过头?的印象。
嬴寒山一下车这位守在城门口的县令就迎了?上来?,他仿佛是诧异地上下打量了?嬴寒山一眼,然后整肃脸上的微笑,后退两步合手再拜。
他说久闻嬴将军武功,未详今日得见,果有天人?之威。
……不是,哥,我当?将军的时长还没?你跑路回来?的时间长。再者说,我出发之前你就应该知道是我来?吧?
嬴寒山默默地os,把手缩回袖子里掐了?一下自己,转移掉寒毛倒竖的尴尬。
苌濯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韩其握着他的手真情实感地称赞了?一通那?位苌姓的太史令,说到他曾经以一言保下淡河时还湿了?湿眼眶。
“仁者不寿啊,”他感叹着,“苌公横遭此难,令人?闻之肝胆摧折。今见苌郎君,有公昔日之风,怎不令人?涕下。”
嬴寒山还在认真思考着这人?到底有没?有见过苌濯他爹,韩县令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刚刚下车的嬴鸦鸦身上。这位满肚子是词儿的仁兄好像突然死机了?几秒。
“这位,这位使?君……?”他斟酌着用词,显然没?想到这位跟着副使?一起来?的书官是位年纪不大的女郎。
她和嬴寒山,苌濯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当?她撩开帘子探出脸颊时,不论谁看到都会觉得她更适合穿着一身颜色鲜嫩的衣裙,头?戴朱钗被乳母丫鬟服侍着下车。
但?她穿着改小了?的男装,作少年人?的发式,与那?个预想中的形象大不相同。
“这是小妹,嬴鸦鸦。”嬴寒山说。
韩其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稍微露出一点光亮。
设宴不是在官府,是在韩其的私宅。
宅子有些像是二十一世纪某些四位数起步的会员制餐厅,院落里疏密地栽植着很多原产地不在这里的草木。
两棵古樟一前一后地覆盖了?大半园中,枝叶伸展,青绿色的叶冠如同华车的羽盖,当?佣人?扫除落叶时,能嗅到空气中淡淡的香樟气息。
传菜的侍女们穿银线绣的烟青褙子,一行一行袅娜地从廊下走来?,布菜,而?后莞尔而?退,像是一群有了?人?形的水鸟,翩翩而?来?,又盈盈而?去。
韩其笑眯眯地劝菜劝酒,余光却一直瞥着嬴寒山。这个年轻女人?一直看着眼前的食案出神,只偶尔喝一杯酒。
她是不喜欢这饭食吗?还是心存警惕?韩其当?然听说了?嬴寒山在水上呼雷召电,施展术法的传说,但?他实在没?往她不吃东西?这方面思考。
眼看着这苌家子尚且愿意与自己交谈两句,嬴寒山却一直一副无甚兴趣的样?子,他皱了?皱眉,眼神示意身边人?。
而?嬴寒山完全没?注意到韩其那?过于多的戏。
她只是在走神。
韩家应该不比裴家显赫?就算是旁支,裴纪堂应该也?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私宅吧?
但?他一天到晚就住在府衙里,甚至一个眼看不到就直接睡书房,实在搞不明?白这个人?的财产持有度。
眼前的东西?好像挺好吃的,环境也?蛮不错的,如果放在二十一世纪这一桌子大概也?挺贵的。但?这副身体没?有食欲,对进食甚至有强烈的抗拒,喝饮料已经是极限。她拿着筷子在山葵酱里戳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下。
又有侍女上来?,双手托着一盘个头?不大的禽类。“此为子鹅炙,”韩其曼声道,“是取白羽鹅雏,以精白米与鱼肉饲至绒羽褪去,取鹅脯以桂花酒酿制,请尝,请尝。”
嬴寒山礼貌地夹了?一块,在盘子里放下了?。
又有一盘上来?,切得极为薄的鱼肉在盘中摆出了?牡丹的花形。“此牡丹鲙也?,取一尺半鲈鱼,以最精处制。”
嬴寒山礼貌地夹了?一片,在盘子里放下了?。
“我是终南之人?,”她说,“白日辟谷,万望见谅。”
韩其立刻笑呵呵地接上话,开始谈起修身之学,大赞辟谷轻身延寿,自己也?心向往之,奈何俗务缠身无力修道,只能羡羡而?不得了?。
酒敬过两巡,堂上开始上舞乐,蒿城周遭已经称得上荒凉,但?这些被豢养在府上的伎人?还是彩衣乌发,雪肤花容,一副升平时的富贵相。
一开始因为嬴寒山什么也?不吃而?稍微有些僵的气氛在乐声中松弛下来?。
韩其一边劝酒一边与苌濯闲聊,问的都是些不太打紧的问题。他问淡河风物,问裴明?府近况可好,问苌濯至淡河已有多久,如今可惯?
又问嬴寒山自终南而?来?,终南何解,风土人?情如何,家中高堂在否。间或夸赞两句嬴寒山赫赫之功。
“将军离家亦旧,不生思乡之心耶?韩某宦游多年,近年才携内子与小子定于蒿城。小子年幼,虽颇知书,但?为人?父者久不在身旁,难免放心不下。”
他自顾自感叹起来?,嬴寒山懵了?一下,脑袋里突然短暂地划过一道电光。
他突然提他儿子干什么?
她余光撇过嬴鸦鸦,嬴鸦鸦用手挡住额头?,似乎是盖住了?一个表情——嬴寒山想明?白了?,嬴寒山选择不接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