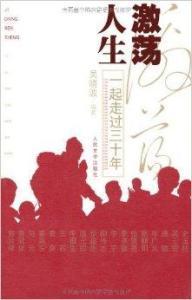最新小说>明月别枝惊鹊 闻檀 > 第25章(第1页)
第25章(第1页)
谢昭宁叫青坞捧了妆奁过来,从里层拿出一枚不起眼的葫芦纹玉佩,这便是大舅舅留给她的信物。前世这枚葫芦纹的玉佩竟是一次也没用过。
谢昭宁将葫芦纹玉佩在手里握了一握,给了红螺,告诉她:“见了此物,他必然信你,他也只信此物,万不可遗失。另外跟钱掌柜说,找寻两个武婢的下落,将她们救回来。”
两个武婢对她忠心耿耿,因白鹭一事被父亲发卖出府了。可她们也是无辜被冤,谢昭宁一定要将她们救回来,这样被发卖了,不知道要去哪里过颠沛流离的日子。救回来后即便不能留在内宅,辟个外院给她们住就是了。
知道此事的重要性,红螺有些紧张,颔首:“娘子,奴婢明白!”
青坞拿了根绳来,红螺将玉佩系了绳绑在衣襟上,藏在贴身的里衣中。
吩咐了二人此事,青坞便给谢昭宁打了水来梳洗。
谢昭宁看着槅扇外渐渐暗下来的夜色,亮起的风灯,想着府中之事。
谢宛宁和谢芷宁只是略微被她打压,并未真的伤及筋骨。而她真正的目的,还是要揭穿白鹭之事,只是究竟要如何揭穿,借力打力,却是个问题。
谢昭宁仍是沉思,眼下这二人势必极其谨慎,她想激这二人出手,露出破绽来。
雪柳阁中仿佛已经安静了,唯独偏门的屋檐下留了一盏豆点大的风灯,叫风吹得晃动,有个小丫头在守夜,靠着梁柱打瞌睡打得头点地。
一个浑身裹在玄色斗篷里的身影靠近了,她竟是独身一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风灯之下。
可这样的动静已经把小丫头给惊醒了,她道:“谁来了?”
那个斗篷下传出一个低柔的女声道:“是我。”
她虽没有露面,但那小丫头却似乎立刻明白了过来,连忙让开了路。
转过一座梁桥,便看到雪柳阁五间的主屋,主屋里还点着灯,在朦胧的夜色中透出暖黄的光芒,此人提步往里走,守着的两个女使自然也不阻拦。等入了屋子,只见谢宛宁正靠在美人榻上看书,伺候她的孙姑自她三岁回府就跟着她,最是熟悉她的习惯,因此烛台都点得亮亮的,叫谢宛宁好看得清书页。这烛光将谢宛宁的脸照得如同莹玉一般微透,微拢的长睫乌黑如墨,雪白的腮线,那红疹已经褪去得差不多了。
此时谢宛宁抬头,便是美人活过来了一般,她的声音在人后透出一种懒散的慵懒,并不像人前那般温和,道:“芷宁,你来了。”
来人摘下了帽帷,叫暖色的烛火一照,果然是谢芷宁。此时她未佩环钗,发亦只是松松一挽,脸上的表情甚是深沉,与平日里有些柔怯的她并不一样。问道:“姐姐身子如何?”
谢宛宁回道:“尚可,喝了药已经不痒了。”又叹道,“今日倒是差些连累了你,幸而成功让你脱身。你可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谢芷宁道:“却也不知,她说是无意遗失被谢明珊捡去,傻了我才信她这话。只是前几日她还听从于我去夺花冠,应该不会这般快怀疑我。”眼睛微眯道,“等我解了禁足,再去试探她一二吧,姐姐莫心急。”
谢宛宁便是一笑,道:“这是自然的,你我姐妹之间怎需说这些。我等你就是了。”
谢芷宁看着谢宛宁在烛火下笑的模样,甚是娇美。
她突然想起谢昭宁的模样,她的肤色如冰雪般,唇不点而朱,尤其是一双极其波光潋滟的猫瞳,若是认真看人时,有种摄人魂魄的惊艳。只是平日她为人太恶,竟没人意识到她生得有多好看。叫她这样的美人全心地看着,恐怕极少有人不会爱上她。
没有人意识到这点。谢芷宁是家中最常与之相处的人,所以当她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她是心神慌乱的。蒋姨娘曾对她说过,她才貌并不算佳,可是谢宛宁不同,凭谢宛宁的才貌,日后高嫁是迟早的事,前途无可限量。
那么谢昭宁呢?
谢芷宁微有些出神的时候,听到谢宛宁柔和的声音说:“这些事,实在是多劳烦你了。”
谢芷宁这才回过神来,不再去想那个荒谬的问题。就凭谢昭宁的修养德行,如今的声名狼藉,哪家的好儿郎会想娶她为妻呢?她这想法当真是可笑。
她也道:“姐姐客气,姨娘曾说过,你我都是一条绳上的。只有合在一起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妹妹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谢昭宁这一夜的睡眠倒是沉稳许多,并未再做噩梦。只是她一贯睡得不多,又习惯了早起。因此也不过是在卯时就睁开了眼。
只见帷幕已经是半挑开了,能看到半挑开的槅扇外,天已经是深蓝,几点寒星散布,青坞和红螺站在院子里,指挥着丫头女使们清扫落叶残枝。
看来昨夜下过了雨。
已经过了卯正,她们为何没唤自己起床?
谢昭宁觉得头有些沉闷的痛,想来是得了风寒。她坐起身来,用手试了下额头,似乎是有些发热。
谢昭宁喊了青坞的名字。
片刻后,青坞撩开帘子和帷幔走进来,手里还擎着一盏烛火,道:“娘子您多睡会儿吧,方才东院那边来传话了,说今日所有娘子的进学和请安都免了。”
谢昭宁记得以往在谢家的日程。若非初一、十五,或者节庆这样去给周氏请安的日子,谢家的娘子们都要在归风堂进学,再去荣芙院给姜氏请安的。
谢家是书香传世之家,一贯重视儿女的教学,规矩也十分严格。
哥哥谢承义如今在边关打仗不说,蒋姨娘庶出的儿子谢承义,年不过十岁,送去了国子监进学。剩下的几个姐妹都在家中进学。要学女训女戒,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不可只做那无知粗妇,说出去不像书香门第家出去的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