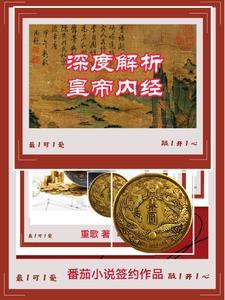最新小说>宦官 > 第8章(第2页)
第8章(第2页)
……
京城,东厂。
换下蟒袍的时鹤书端坐在太师椅上,看向身前的青年。
“竹青,查的怎么样了。”
竹青的脸色有些难看:“不太好,督主。”
身为时鹤书的亲信,在东厂负责收集信息的竹青还是第一次碰壁。
他将收集到的情报盛给时鹤书,时鹤书翻看几页,放到桌上。
“都是陈词滥调。”
竹青低低应声:“这些情报烛阴都能背下来了,属下也派人去了那人家乡探查,可得到的都是同一套说辞。”
但雁过留痕,只要是做过的事,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什么都查不到……
怎么会呢。
竹青几近抓狂,却又不能表露出来。
指尖轻叩桌面,默了半晌后,时鹤书道:“既然查不到,那就先不要查了。”
“你近日也辛苦了,”时鹤书看向黑眼圈几乎落地的竹青:“好好休息。”
神异
“不过是个没根的东西!”
茶盏清脆落地,太后明艳的脸上满是阴霾。
骂督主的话那些太监宫女都不敢接,他们只得跪地磕头,连道“太后息怒”。
“九千岁……呵。”
当今圣上年幼,奏章审阅便倾数交给了司礼监。而也是因当今圣上年幼,秉笔一职空悬,多数奏章都是由时鹤书一人批红,一人盖印。
这样的权利几乎可以称为代皇帝,宫里已渐渐有了九千岁的称呼。
“……罢了,罢了。”
太后的手攥紧又松开:“一个阉宦,任他权势滔天,也做不了真的皇帝。”
“且他一个病秧子……”凤眸微眯,太后冷笑出声:“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到几时。”
京城,督主府。
白帕抵唇,低低的咳嗽声响起,喉间腥气翻涌向上。
丝丝缕缕的红印在帕子上,自回朝后已连着几日都未曾好好歇息的时鹤书再度咳出了血。
注视着帕上的血迹,感受着胸口的隐痛,时鹤书终是站起了身。
他该休息了。
达官显贵的睡前工作大多繁琐,时鹤书倒不至于此。在简单的洗漱更衣后,他便身着寝衣,端正的躺在了榻上。
月光冷冷的洒在他身上,清浅的呼吸渐渐绵长,垂下的鸦羽在脸上投下浅淡的影子,俨然一副安眠模样。
“咚!”
忽然,重物落地声闷闷传出,紧闭的室内多了道呼吸。
若有人亲眼见证了方才那一幕,定会惊愕到说不出话来。毕竟那可是一个活人凭空出现,且险些跌到了榻上!
景云没想到系统会把他直接传到床上,还是躺着时鹤书的床上。因此在落地时紧急打了个滚,把自己滚到了地上。